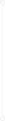修改时间:2018-10-30 10:05:43 浏览次数:12023次
阿里巴巴一直都很孤独。
19年前,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在做门户,只有阿里巴巴在给中小卖家搭建交易网络,被同行嘲笑没技术含量,是“鼠标+水泥”的脏活儿。15年前,互联网泡沫劫后余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大多盯住了短信和彩铃,阿里巴巴开始做淘宝,进而又推出支付宝,让普通人把东西卖给普通人,也不被看好。11年前,阿里巴巴B2B业务在香港上市,波澜不惊,股价不好看,也没什么人关注。那会儿中国互联网界普遍高举“web2.0”的伟大旗帜,都等着围观腾讯和百度怎么围绕着这面旗帜争个圣杯的输赢,人人网和开心网红得发紫,360和迅雷被众星捧月。8年前的3Q大战,卷进去了腾讯、360和整个金山系。7年前的搜索新战场让百度和360正式全面交恶——而阿里巴巴,一直在众声喧哗之侧。
 创办伊始的阿里巴巴,在马云的湖畔花园16幢1单元202室开会
创办伊始的阿里巴巴,在马云的湖畔花园16幢1单元202室开会
可以说,直到2011年,在中国互联网业界大部分骨灰级人士的心中,阿里巴巴都是一个特殊而且挺别扭的存在,你不能忽略它的地位,但它偏安杭州,做的事儿跟大家不一样,气质也跟大家不一样,创始人长得也跟大家不太一样,喜欢论剑谈道,天马行空,不喜欢谈技术和产品,互联网精英们看不懂,也聊不来。
直到2012年“BAT”称谓横空出世,很多中国互联网界的头面人物才终于不得不承认:一路做中小卖家网站、电商和支付起家的阿里巴巴,不仅成了寡头之一,而且你绕不过去,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讨论,不得不研究。
但是,阿里巴巴还是很孤独。它想把支付宝从VIE框架中剥离出来,跟雅虎交恶,中国互联网界一边倒地指责阿里巴巴缺乏“契约精神“。3Q大战之后,腾讯凭微信再度获得中国互联网从用户到舆论场上的支配性地位,2013年上半年,借着春节红包和网约车,微信支付一举拿下了支付宝的大量用户,大多数互联网从业者都觉得阿里遭遇重大挫败,逐渐无法与腾讯抗衡,因为它太虚,不重视产品体验,咎由自取。2013年底,阿里巴巴推出“合伙人制度”,因为“同股不同权”的制度设计与香港交易所发生龃龉,大多数对Google、Facebook甚至百度采取“同股不同权”体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并无异议的中国互联网业内人士,批评阿里巴巴损害了投资者利益。2014年之后,以战略投资京东为标志,腾讯投资了阿里巴巴的几乎所有对手,并在2015年把美团“策反”成阿里最坚定的敌人。业界流行的看法是:腾讯得道,所以多助;阿里失道,所以寡助——将这个看法诠释到极致的,是2017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那场著名饭局:以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同志为核心,腾讯的朋友、也就是阿里的敌人们坐在了一起——这是中国互联网的大半壁江山。而马云形单影只,不在任何饭局的名单上。
 2017年乌镇峰会期间著名的一场饭局,团结了中国互联网的大半壁江山,没有马云
2017年乌镇峰会期间著名的一场饭局,团结了中国互联网的大半壁江山,没有马云
现在,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宣布要退休了,这种孤独感更是被舆论推到了极致:“树大招风”、“他怕了”、“民营经济的危险信号”……一个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成了整个民营经济的公共舆论风向标,也成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异数,既是高处不胜寒,也是置于炉火炙烤。
阿里巴巴被误读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普罗大众对阿里巴巴的和“马爸爸”的成功学想象是一种误读,知识界和商界对阿里巴巴“民营企业风向标”的定义是一种误读,而更深的误读,来自阿里巴巴的所在的行业——中国互联网业界对阿里从本能疏离,到被动重视,再到集体质疑,进而到现在的沉默接受,就是因为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阿里巴巴一直是非我族类的“他者”。
随着中国互联网秩序的另一极腾讯在2018年面临的阶段性困境,可能会有更多人试图尝试理解和接近阿里巴巴这个“他者”,但是阿里巴巴的孤独将是持久的——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20年历史上,只有阿里巴巴是“碰巧成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存在,这也是阿里巴巴一系列孤独的根源。
孤独的生意人
社交媒体上一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段子:马云去酒吧闲坐,结帐的时候刷的是信用卡,而非支付宝。而马云自己也公开说过,他其实不用支付宝。
这个段子在2016年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竞争中显出疲态的那段时间,经常被中国互联网精英拿出来说事儿: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重视产品和用户体验,难怪支付宝做不好,被微信追着打。你看腾讯的小马哥,陪同官员视察腾讯的时候眼睛还紧盯着白板上的产品排期表,人家这才是重视产品,难怪微信和王者荣耀都那么厉害。你再看雷军,一谈起小米的产品来就滔滔不绝。可是阿里和马云呢?每当阿里巴巴推出了一款失败的产品,“阿里不懂产品,马云不懂技术”就会被拿出来鞭打一遍。操作系统YunOS的时候如此,社交工具“来往”如此,支付宝几次蹩脚的改版亦如此。
 微信和支付宝2013-2014年的大战被普遍认为是阿里巴巴的败绩,但真实情况呢?
微信和支付宝2013-2014年的大战被普遍认为是阿里巴巴的败绩,但真实情况呢?
不过话说回来,支付宝被微信追着打了好几年,微信赢了么?
在2018年湖畔大学的一次内部分享上,马云复盘过这件事:“2013年,微信如日中天,我们想搞一下,结果门牙掉了两颗。过了几年到现在看,我们可以说肩并肩了,还不包括蚂蚁和菜鸟。”
的确,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在微信群抢红包,看到付款的二维码会本能地打开微信,支付宝确实因此失掉了一部分城池,这就是马云打比方的掉了的那两颗门牙。但“借呗”弄点零花钱周转,“花呗”分期付个款,余额宝做点小规模定投,芝麻信用分数给房贷、车贷和签证时的信用背书——在过去的两年,这些业务没有因为微信在支付环节的崛起而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强了。只要涉及到消费金融服务领域,腾讯抑或是腾讯扶持下的京东,都不能跟阿里体系下的蚂蚁金服比肩。
微信在“支付”这一个动作上碾压了支付宝,它做好了一款产品的一个功能。而蚂蚁金服依托支付宝,掌握着中国的消费金融服务命脉,它做的不是一款产品,更不是一个功能,而是一个生意,一个把中国人的消费和金融行为数字化的生意。
而“做生意”这件事,其实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精英人物们不太瞧得上的。
在中国互联网的江湖里,一个人如果被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产品经理”,那简直是圣杯之巅的荣耀,比如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和“微信之父”张小龙,都因为“懂产品”而极受推崇,360创始人周鸿祎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技术天才,也是开山立派的地位,比如搜狗的CEO王小川。但假如一个人的标签是“生意人”,大家对他的评价就很暧昧。
而阿里巴巴一开始的愿景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早年的B2B,到淘宝和天猫,再到蚂蚁金服,再到“新零售”的盒马鲜生,从毛孔到血液,都是交易、贸易和生意。别人是搞算法的、写代码的、雕琢产品细节的,您是做生意的和卖货的——在中国互联网江湖的隐性鄙视链上,地位就已经垫底了。
 是一家技术公司还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始终是中国互联网界对阿里巴巴误解的来源
是一家技术公司还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始终是中国互联网界对阿里巴巴误解的来源
其实自从2014年以来,阿里巴巴在商品算法推荐、云计算、城市大脑、智慧物流、AI应用和生物识别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国内甚至全球相当领先的水准,但只要它被隐藏在了天猫双十一的包裹峰值数据、盒马鲜生的零售货架和蚂蚁金服的信贷理财背后,而不是露在外面的肌肉。那些推崇极客精神和产品导向的中国互联网精英们,就仍觉得阿里巴巴是不是一家真正技术驱动的公司,一句“还是得看创始人的出身”就把它打回原形。
马云不是工程师,更不是产品经理,他的接班人逍遥子(张勇)也不是。这在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当中极其罕见。马化腾、雷军、李彦宏和周鸿祎他们都是能自己撸起袖子写代码改产品文档的,马云不能,他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是科技公司创始人当中的“黑五类”,更何况这位厉害的英语马老师还经常公开地表达他对技术的困惑——2017年5月乌镇的人机围棋大战,柯洁对战AlphaGo落败,当时马云在数博会的机器智能高峰论坛上说了另一番话:“这几天的人机大战比较热闹,我觉得人类是最有意思的动物,在AlphaGo和人类下围棋之前,在网上绝大部分人认为机器肯定会被人搞死掉,打输了以后所有人都认为机器一定会搞死人,我们这么颠来倒去的‘认为’,我并不以为然,尤其中国我们很多公司别再去搞AlphaGo这样的东西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段话一传出,又是业界一番批判。几个月之后,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专攻前沿基础科学,一些技术精英们谨慎悲观。一个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搞前沿基础科学,总是让人觉得缺乏真诚感。
这些定见的背后,是一个中国互联网20年以来被事实上奉为“政治正确”的理念: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必须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技术和产品毫无保留的痴迷与热爱。哪怕这些技术的背后只有一套精美的PPT或是其它圈钱的幌子——乐视和法乐第的创始人贾跃亭以及一众以区块链之名发币割韭菜的“大佬”都在忘我地演绎他们对技术的狂热和对产品的痴迷。
与此同时,一套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逻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应该专注于用先进的技术,研发一款杀手级的产品,满足人们的某一种需求。只要这款产品有了海量的用户,就有了流量,进而就成了平台,商业模式水到渠成。无论腾讯、百度、360、今日头条还是小米,都是靠一款产品起家,进而推出多款产品,获得了国民数量级别的用户,变成了流量入口和平台巨头,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但阿里巴巴的逻辑大相径庭。阿里巴巴从来不标榜“技术至上”(这两年有一些变化),马云觉得AlphaGo“没意义”,这话让技术精英很伤心,很愤怒,也遮蔽了阿里巴巴对前沿科学和技术研发的真实投入——2017年阿里的技术投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高于腾讯的130亿和百度的120亿,阿里在安全、算法和AI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储备也是最多的——但技术和产品,不是阿里的牌坊。
阿里的“套路”是:先定义这是一个什么生意,再看这个生意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哪些技术能实现它。它认为中小企业建网站是个生意,鼠标加水泥就够了。它相信个人卖家的电商时代要来了,就有了淘宝;它希望控制整个的支付环节,就有了支付宝;淘宝假货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知名品牌也接受了电子商务,就有了天猫和双十一;支付宝积累了网购消费的数据,分期付款和信贷能促进人们的电商消费,也能成为独立的生意,就有了借呗和花呗;人们的消费和信贷数据有了历史记录能支持下一步的消费,就有了芝麻信用积分,进而产生了更智能的算法模型;双十一的交易量并发撑坏了服务器,就有了“飞天”计划和后来的阿里云;庞大的网络交易吞吐让包裹川流不息,就有了自建的物流网络菜鸟,背后必须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支持物流更科学的配送。线下的商店和卖场需要被互联网的消费习惯撬动,就有了“新零售”的盒马鲜生和升级版的大润发,就需要靠图像识别、增强现实和动态定位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以“新零售”为例,它是一种新的商业形态,背后是几十款APP,几百家门店,以及多重复合的前沿技术组合——但它首先是必须是个生意。
 驱动新零售的是技术,但新零售的形态是商业
驱动新零售的是技术,但新零售的形态是商业
百度宣称以技术为最高信仰,腾讯宣称“内容”和“连接”是基因,都是技术和产品的话语体系,而阿里巴巴的使命是创造“经济体”——这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阿里巴巴的话语体系不是科技和互联网的,而是商业和生意的。
记得阿里巴巴的首席技术官张剑锋(行癫)曾经感慨,阿里巴巴在商业上的成功掩盖了他技术上的实力和投入。这对他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委屈,但接下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2018年,此刻当下,中国互联网发展来了20多年,正在前所未有地拥抱“产业化”。单一的产品和技术对一家规模化的科技企业来说不再重要,如何用技术和互联网实现某一个产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成了最它们核心的任务——这也就是所谓的“产业互联网”。其实,产业即商业,产业即生意,产业即经济体。腾讯最近调整了组织架构,宣布要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其实,消费何尝不是产业的一部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之间没有楚河汉界,只有“以技术为本”和“以生意为本”的思维差异。
当中国互联网正主动或被动地集体告别“技术原教旨主义”和“产品原教旨主义”的时候,阿里巴巴是不需要告别什么的。
孤独的文化认同
明白了阿里巴巴的话语逻辑是商业而非科技的,也有助于理解备受争议的阿里巴巴文化。
喜欢阿里文化的人觉得它出神入化,讨厌它的人直斥其为洗脑和忽悠。但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众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当中,它属于一种“异质文化”,难以复刻,不可习得。
从形式上,阿里巴巴文化的异质性有很多显露在外、为人熟知的细节:太极、禅文化、员工“花名”、武侠小说元素命名的会议室、从“独孤九剑”到“六脉神剑”的价值观提炼、具有高度话语权的HR“政委”体系,“要做一家102年公司“……这是一套中年男人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趣味,年轻人占多数的互联网从业者可能会产生不适感,这也是阿里巴巴的文化在技术和产品经理的圈子里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武侠文化”和“革命文化”是人们从表象上理解阿里巴巴文化的两个典型标签
“武侠文化”和“革命文化”是人们从表象上理解阿里巴巴文化的两个典型标签
但阿里巴巴的确是一家挺“留得住人”的公司。一些人闻阿里文化而逃,怕被洗脑,但很多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被收购的创业公司创始人,都在阿里巴巴扎住了脚。有人说阿里巴巴的文化就是创始人的文化,马云喜好武侠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情有独钟,所以阿里的文化也是这个气质。但他们可能忘了,马云的英语表达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当中最好的,阿里巴巴有数千海外员工和外籍员工,美国西海岸就有5个办公室。阿里巴巴的文化特别容易被标签化,因为任何一个标签都很显眼,但这正是误读的根源。
其实,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构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最不同的地方是:它一点“硅谷执念”都没有。
硅谷一直是中国科技从业者的麦加,“硅谷精神”也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和企业家的情结和迷思。当人们提及一家互联网公司有“硅谷基因”,意思是它在某些地方很像苹果、Google或Facebook,是一种赞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很热衷把自己装扮成一家硅谷企业——大家喜欢把挂在Facebook园区里的标语“Go Big or Go Home”翻译成中文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是挂个海盗旗;学习Google提供免费午餐和健身房,复制“80:20”的时间分配原则,用工作时间搞黑客马拉松;创始人喜欢管自己叫“首席产品经理”和“首席增长官”,坚持每周敲几行代码; CEO和高级管理人员坚持跟员工们一起坐在开放不设隔断的大空间里;开发布会的时候不忘用穿套头衫和牛仔裤的仪式致敬乔布斯;喜欢谈“极客精神”和“黑客之道”。小米创始人雷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专注、极致、口碑、快”互联网七字诀,其实都是硅谷的日常口头禅,雷军也从不讳言,从金山到小米,支持他一路走过来的精神信念,是大学时候看的那本《硅谷之火》。
 中国互联网公司热衷并擅长在形式上模仿硅谷公司
中国互联网公司热衷并擅长在形式上模仿硅谷公司
推崇“硅谷精神”,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文化正确。但当硅谷的那一套让他们觉得麻烦的时候,他们就说“硅谷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多数事上做得其实不那么硅谷: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为了招聘更多的死宅工程师,让漂亮的女性HR和产品经理扮演“程序员安慰师”,这在硅谷是要上法庭的,但中国互联网企业热衷此道。大家在市场竞争上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封杀对手的API接口、恶意举报,买流量掀起口水战,但照样把“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硅谷门神贴在表面上。
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对硅谷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也是表象的。人们习惯认为“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理念是硅谷精神的核心,但这一套放在硅谷之光的苹果,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人们提到黑客精神和极客精神,经常会想到Google和Facebook,但其实Google和Facebook的文化大相径庭。在旧金山两家位置临近的“分享经济”的代表公司——Airbnb和Uber的气质更是由内而外的不同。而硅谷之外的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些硅谷内在的分裂和差异性,而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和想象建构另一个“整体上的硅谷”,也热衷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复制另一个硅谷。
热衷在中国互联网世界想象和建构硅谷的人们更忽略了一点:硅谷既是一种生态建构,更是一种文化建构。硅谷既是科技从业者、大公司、创业公司、VC、孵化器和高校在一起的有机体,也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产物。硅谷精神的内核,与反战、嬉皮士、性别和族群平等、禁欲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50年以来的人类思想实验是一体的——而这是在当代中国难以建构,也学不太像的。
 硅谷精神发端于嬉皮士运动、反战和无政府主义等1960年代的美国人文思想实验
硅谷精神发端于嬉皮士运动、反战和无政府主义等1960年代的美国人文思想实验
缺乏文化认同的浅表式硅谷模仿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没文化。号称有文化而员工们不相信、不实践,说一套做一套,也是没文化。越学硅谷,就越不像硅谷。20年前就从硅谷回来的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跟两年前刚从硅谷回来的陆奇尝试着共事了一下,很快就散伙了。这背后的冲突本质是文化冲突,两种成色不同的“硅谷文化”之间的冲突。
相比之下,腾讯是有文化的,也深得不少互联网从业者的喜欢,但自从“腾讯没有梦想”之后,连腾讯自己也质疑自己的文化——腾讯的文化症结源自其内在的冲突:一半是有着类硅谷基因的产品经理文化,另一半是有着类华尔街基因的投行和咨询顾问文化,腾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存在是缺失的,也让它看上去“没有梦想”。
而阿里巴巴的文化存在感,就很鲜明而孤独了。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阿里的文化建构来自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不是1960年代的美国西海岸,没有反战、嬉皮士运动、族群平等和禁欲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是: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明的推崇,个性解放,个体对生活不断进阶和获得成功的向往——这是阿里巴巴建构自身文化的根基。
阿里巴巴的文化基因天然不存在太多硅谷的元素,但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深刻,它需要一整套标签和仪式感来呈现这种文化。对公众,它有以“双十一全球购物狂欢节”为标志的消费主义和商业乐观主义的文化标签,也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的个人进阶和成功学咒语。对阿里内部,它形成了一套有效率地推动实现其商业目标的运作机制和组织文化,最初设计阿里巴巴组织文化的前任总裁兼COO关明生是香港人,来自GE,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最早期的职业经理人,他设计的一整套阿里巴巴的管理机制是现代化的,它背后的伦理和文化只能是现代化的,但在阿里巴巴,这种现代伦理和文化落地的形式感是很中国的:它既包括强烈革命时代色彩的“政委”体系架构和背后的一套革命色彩话语,也包含了太极、禅、武侠和“花名”等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科技界的很多人不喜欢这套文化符号,觉得它与崇尚颠覆、鼓励开放、平等和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必须得承认的是:对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年轻的一代中国人甚至大部分生于中国、受教育在中国和成长在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来说,革命色彩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庙堂化的民间文化元素,是注入在文化基因里的。在人和人的沟通中,文化就是可以通过“意会”而通关的那一部分,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独孤九剑”的认知直觉肯定比“嬉皮士运动”深刻,对“延安精神”的理解也精准于“黑客之道”,这是一个基于文化的事实,也是很多当代中国人自我回避、不愿意承认的文化事实。
因此,阿里巴巴在文化基因上需要中国,不需要硅谷。
越是在美国和硅谷生活过的中国人,越是在多元化的环境下工作过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属性越有真切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来自GE和宝洁的职业经理人,从Facebook、Google和美国高等院校回来的科学家,以及被收购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阿里留下来的原因。反而越是对硅谷有着远距离遥望式崇拜,对自己的文化基因下意识逃避,对“意识形态”有着应激反应式抵触的圈子里的年轻人,对阿里巴巴的这套文化越反感。
阿里巴巴是有意识形态的,但Google也是有意识形态的。Google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技术如何在“不作恶”的原则下重塑世界的信息整合规则,阿里巴巴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推崇全球化的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阿里巴巴意识形态并不是中国庙堂式的和红色革命式的,否则不会产生超级碗式全民狂欢的“天猫双十一”和娱乐至死的内部年会。但革命时代的组织架构和话语体系在能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阿里巴巴实现商业愿景的方面,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而太极、禅和武侠的传统文化的民间元素又消解了革命话语的庄重性和压迫感,包容了个性,让每个人可以做自己,让它变得更像一家科技公司,为它赋予了非正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代科幻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的精神相通就在于此。
 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构基础是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和商业进步主义
阿里巴巴的文化建构基础是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和商业进步主义
选择用武侠和禅意的方式,还是科幻和极客的方式阐释梦想,是一种选择之道,而阿里巴巴的道路是相对孤独的。这当然来自马云的自身文化偏好和底色,但也是一种文化自信。中国互联网公司和它们的创始人普遍缺乏的就是文化自信,学硅谷和跨国公司的皮毛装点自己,最后还是没文化。文化是一家公司的标签,一家没有文化的公司,在走向全球市场的道路上注定是磕绊和艰难的,但一家内核里推崇全球商业文明,表象上呈现中国式文化元素的公司,反倒是一家最全球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最近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话语体系调整,明显朝着“中国化”的方向演进,比如小米,它设立了组织部和参谋部,在故宫开发布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未来可能有更多公司会这么做,但文化底色上的东西,是难以复刻的。
孤独的历史定位
2018年是阿里巴巴微妙的一年。
大环境对它并不差:业界对阿里巴巴质疑少了,“阿里巴巴不如腾讯”的论调没了,美股大跌阿里巴巴的市值也缩水了30%以上,但从财报看,它是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当中唯一收入增长超过50%的,其中与“新零售”相关的业务增长超过340%,应该也是当下中国成长性最好的科技公司。不过马云要退休了,一年为期的交接,退休后从事公益和教育。
人们猜测马云的退休原因,担忧阿里巴巴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为什么退休?阿里巴巴今后是谁的?终于交给国家了?马云退休是民营经济的危险信号?马云自己出来解释了好几次,但解释没有用。
阿里巴巴和马云一向是中国互联网新经济,乃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存在,也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在科技和新经济企业当中,它最有整体社会和经济意义的代表性;在众多民营企业当中,它的存在挑战了颠覆了另一些传统玩家的存在;在整个企业家群体当中,马云会见的不同国家的总统和总理数量最多,把贸易和政治融在了一起,看上去最“政治”,但他又是中国顶级的民营企业家当中罕见没有政治头衔的——既非全国人大代表,也非全国政协委员。对一些敏感议题,比如企业的所有制属性,马云直接回应“阿里巴巴是国家企业”,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不敢,因为这势必引起争议和猜测,事实也果然如此。
有关“阿里巴巴是一家什么企业”和“马云为什么要退休”,其实是一个问题的A面和B面,它涉及到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当中,马云可能是“历史感”最强的一个人。中国大部分技术和产品出身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和企业家,都是活在当下的,当然也有未来的愿景——但愿景不等于历史感,如果它不能超越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甚至更久远广阔的时空而存在的话。
早在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马云就提出“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至少跨越三个世纪。至于102年之后的阿里巴巴什么样?马云肯定不知道。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愿景应该还在——22世纪商业是仍然存在的,但可能云计算、新零售甚至人工智能都不存在了。为自己无法预知的未来制定计划和安排,就是历史感。
而阿里巴巴和马云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形成,发生在2013-2014年。
2013年,马云卸下阿里巴巴CEO一职,交棒给了陆兆禧。同一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合伙人制度”,并计划在香港重新上市,触发了与香港交易所“同股不同权”的理念之争。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当年底,马云在出席杭州市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联席会议时表示:“我们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国家企业’”。
 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历史定位,在2014年美国上市的前后基本就清晰了
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历史定位,在2014年美国上市的前后基本就清晰了
现在看,阿里巴巴未来往哪儿走,马云接下来要做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国家企业”是一个容易引发联想的词汇,尤其是在中国。过去40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分野和争论放大了人们对“国家企业”的联想甚至不安。其实,“国家企业”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马云也解释过:“就像三星是韩国的国家企业、奔驰是德国的国家企业、谷歌和苹果是美国的国家企业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诞生一批能代表中国的年轻人,代表中国的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代表这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的国家企业”。
从全球范围看,“国家企业”应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它得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和指标效应,它得能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和竞争力的商业标签,它还得是一家“全球企业”,在海外有商业甚至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布局。中国能成为“国家企业”的公司并不多,阿里巴巴还真的是。
但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企业”也有另一些阿里巴巴尚未完全具备的共性:它们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在它们成立的历史时代具备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经历过多次技术、经济和历史的时代变革,业务发生多次根本转型。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企业”已经都退出了创始人主导公司发展的阶段,取而代之以职业经理人或家族接班人团队管理公司,而且“国家意志”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方向选择,必要的时候会出面干预或施以援手,企业并不能自生自灭和自己决定一切——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韩国的三星、日本的富士通和美国的GE,都是如此。
中国还没有持续历史超过40年的民营企业,"要做一家102的公司”的“国家企业”阿里巴巴,能摆脱诺基亚、爱立信、GE和三星们的历史共性么。
清楚了“国家企业”的历史宿命,你就可以更理解为什么在马云交棒CEO的同时,阿里巴巴推出了“合伙人制度”——它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创始人退休设计的。在创始人淡出日常决策和管理之后,合伙人制度就是阿里巴巴高层管理团队、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平衡仪,合伙人制度的弹性和开放性,能保证阿里巴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运营独立,能实现它作为一家公众公司的治理透明,也能落实它作为一个“国家企业”的任务和使命。

阿里巴巴可能是中国最典型的“国家企业”了
作为国家企业,既然它的商业愿景势必与国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融合;既然它得存在至少102年,最终变成一家业务格局与创建伊始面目全非的公司;既然它的创始人早晚得淡出公司的具体经营——类似的事从150年前到现在,在欧洲、美国和东亚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那么作为阿里巴巴,作为马云本人,应该怎么做呢?
对即将大多数精力投身公益和教育事业的马云来说,比尔 盖茨似乎是个非常好的role model,但人们还记得他是微软的创始人,迄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认为微软是他的。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拉的长久一些,通用电气(GE)作为美国的“国家企业”,已经有139年的历史了,它的创始人叫托马斯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个世界上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大家好像都不认为GE是他的。他被世界记住的,是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另一个身份。

美国的"国家企业"——通用电气(GE),创始人是托马斯 爱迪生,但现在没人想得起GE是他的,但都知道他是个发明家
站在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新硅谷20年的历史坐标看,创始人退休是一件极为反常的事;站在以英特尔和苹果为代表的旧硅谷50年的历史坐标看,创始人退休甚至去世,是一个历史规律;站在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以来近200年的商业文明史进程角度看,总有一些企业成为时代的一部分和某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它被融入了人类的科技史、商业史、国家史和国际交流史,而它的创始人是谁,曾经很重要,后来已经不重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也是孤独的。个人奋斗加上历史进程让它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国家企业”,也让它在只有40年历史的中国商业话语体系尚未做好接受“国家企业”形态的时候,成了被质疑、误读和猜测的靶子。而这种孤独,注定将是更长久的。(来源:PingWest品玩 作者:骆轶航)
下一篇:绕不开的双十一 降不了的快递费